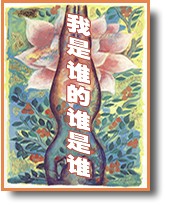谁的青春有我狂-第19部分
按键盘上方向键 ← 或 → 可快速上下翻页,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,按键盘上方向键 ↑ 可回到本页顶部!
————未阅读完?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!
我对小云只有恨没有爱,她要是跟燕燕来看我,我让她怎么进来,怎么把她轰出去。
自然,小云不会被我轰出去,因为她根本没来看我。
笔是一声霹雳的锋芒 电话是倾吐声音的爱恋
学校里已经临近期末考试,大家都在紧张复习。在这个时候,有位春风牡丹人与我交了朋友,她就是天儿。
天儿的父母与我父母认识,从小就有来往,但我太小,不记得。在我初一时,她曾和我一起去滑过雪,当然我是所有人里最不灵活的,基本上是从山顶滚到山底。而且好不容易爬到山顶,没几秒钟就下去了,让我觉得很不划算。
那次活动不知怎的,我如中了魔般,极其开朗爱说,积极与众人握手笑谈,天儿坐在我前边,我与她聊了很多。她看的次数最多的书是《红楼梦》,其次是《神雕侠侣》,极爱曹雪芹,对金庸的书如数家珍,还痴迷周星驰的电影。这样分裂的人,我从没见过。悠哉悠哉(9) 那次滑雪后,我们根本没联系。这样过了一年,去301医院前在家休养的那几天,妈妈联系让天儿来家里与我聊《红楼梦》。
《红楼梦》我是知道的,可过去读它的记忆已经一片模糊,要想与这位“劲敌”谈几个小时而不倒,就必须得用上唬人的演技。 天儿与她妈妈准时来了,她高高个子,皮肤黑黑的,得体时尚的衣服穿在身上很合身。还是一年前滑雪的样子。我与她对坐,大观园景色被我们言谈间跑了个遍。她的表情常不动声色,心里像揣着什么惊喜,大眼睛躲在镜片后,连微微一笑都是狡猾的。我与她谈话时每一个举动都是经过百般考虑才做出的,稍有差错,就会被她识破我的外行,比如:
“你知道《红楼梦》里有个某某人吗?”
“她呀!”我一甩手,一扬脖,好像很懂的意思,“就她呀!对,知道,不就是她吗!”心里还在想这个人到底是哪一回出现的。
据说阮籍见礼俗之人给白眼,遇到志趣相投者,就给青眼,后来青眼就成了互相尊重的意思。那这么说,我与天儿就要互相对给许多青眼。我们有太多的话题可以分享。听说天儿对于学校的学习有很多苦恼,我更是有患难知己的想法,学校之苦闷我体会最深。我是从小学一年级就一直吃力学过来的人,偶然的发病及时将我解救,不然要是继续苦闷压抑、日复一日地考试下去,我仍会发病,只不过发病原因不一样而已。
这么神奇的女孩儿,女生里难得有此爱好,可她又不沉闷迂腐,而是轻灵的作为。经历上又复杂古怪,像我。男生里一万个也出不了一个我,她于女生也是如此。千万不能用纯洁淑女的形象想像她,她的鬼主意多着呢!
话题回到301医院,在期末考试临近时,她用一种大无畏的勇气,坚持天天给我打电话,隔三差五晚上就和天儿妈往医院跑。
天儿把曾经谈话中提到过的一瓶汽水带给我,又给了我一本《男孩来自火星,女孩来自金星》,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搭配关系,我记不清楚了。她还带来一本书,将红楼梦诗词收录全了,那本书她包了皮,但书皮薄如纱,我屡屡翻阅,但也小心没有将其弄破。
我喜欢穿怪异的衣服,天儿痴迷cosplay,好像是动漫社还是什么,我对她的那些事情极其不明白。她听说我的这种喜好,就告诉我有地方能租,我自然欣喜若狂。我们商量着她来贞子的打扮,我来绝地武士的打扮,两人上街一起去看《星战前传3》。有一次和天儿通话我说:跟你打电话像吸毒。天儿说:吸毒是物质的。我说:那我就是精神吸毒。
病房里我感受到了她的关心,还因为我们同样面临着困难。考试是她的心头大患,肿瘤是我的胸头大患。天儿痛苦地告诉我,说她们快要期末考试了,我笑着解释期末就是期待末日,她忙改口说一般称其为期终考试,我又说那就是期待终结。倒也形象描述了她的处境。
每次她来,我们就在病房楼道里遛弯,聊天,我给她讲了一个笑话,说黛玉葬花其实是在偷偷把她打碎的花瓶埋起来,她笑。她说:“女生都会喜欢你,第一,你有文才,第二,你说话幽默,第三,你长得也不丑。”我听了,非常高兴。临分别时,趁家长们在聊天时,我紧紧地搂了她一下。
那阵子,几乎天天下雨,这些无端轻薄的雨,吹得我反而越来越胖,满脸是包,是整个生病期间最胖的时候。王钊有一次来看我也碰到天儿,我问他天儿好不好?只可惜王钊读古书太多,对女人有天生的歧视偏见,不像我。我声称但凡有女权游行,我肯定是举着旗子走在最前头的。
白天,我独自在病房读《红楼梦》,见书里描写宝玉挨打,全家热闹成一团,他躺在床上,黛玉和宝钗皆来探望的情景,不由联想到自己,在书上记下了自己的感想。“我现在的感受是挨了贾政打的宝玉,他们这般关心我生病,到时就是我死了,也定是心满意足,无可遗憾……”悠哉悠哉(10) 6月25日,星期五,我就要“上刑场”了,之前最后一次盛大的“探监”不能不提。老师倾尽全力,带了许多人来,可医院是何等戒备森严之地?我们就相约后花园见,电话里使劲嘱咐老师不要带太多人,别把防暴警察招来。
星期三下午,我睡完觉让爸爸带着去洗澡,穿上新衣服,包了头巾,一身都很漂亮。 这一日,好花好天气,我让爸爸拿摄像机在旁边拍下了全过程,大家见我只会笑,凑到跟前也说不出一句话,都自顾自玩耍。王钊和男生们坐那儿聊足球,女生们坐到更远的地方。小云一个人站在树旁。妈妈把我推到小云跟前,此时我们已经近一个月没有见面了。
我坐着轮椅在小云身旁,四目深情,却无话可说,《红楼梦》里宝玉黛玉久别,重新相逢,无言良久,才吐出句:“宝玉,你好。”这种简单,却有无数凄凉。不过时代真是不一样了,我不会说:“小云,你好。”而是对她说,“我一直觉得你的脸像一只桃子。”
其时我呼吸已经困难,说起话来很艰难。但也若无其事地与小云说了几句,妈妈又把我推到众女生跟前,小云也跟了过来。我还是平时谈笑风生的样子。我告诉她们:“在医院我不喜欢穿病号服,所以这个时候仍是穿休闲服装。”女生们把我围成一圈,我在里头给她们说英文,让她们解释lover等词语的意思。她们是班里头的精英女生,与那边聊天着的精英男生都关系错综复杂,有很多传说的暗恋事件。
男生和女生都在一起照了相,不知怎的,小云那天所有的照片表情都很难看。其他人都好看,尤其是小辉,她已经笑开了花。我在13岁文集里曾写:
“一次在体育课上锻炼时,看见小辉坐在乒乓球台上,一色红衣,眼睛调皮地望着服装呆板的男女学生,异常惹眼。看胡兰成的小说,其实是在看他的自大和自我欣赏,不管人家女的因为他哭成什么样,他也只说出一个艳字,好像这人终生为艳而活着,但他的艳是他自己的。看看小辉坐在乒乓球台上的样子,才是真正的艳,更何况那一色红是燃烧在蓝白相间的校服群中。”
她肯定还记得我的这些文字,301医院期间,她天天放学后给我打电话,也聊到了这些事情。她是我上初一以后在这个班留心过的第二个女生,第一个女生叫晓晓,曾经是马勃喜欢的女生(你瞧这个关系多乱)。留心晓晓的原因是我觉得她像电视剧里的林黛玉。
集体照照完了,我开始和男生们拥抱,可惜没照下来。我从轮椅上站起来,顿时女生们一片惊呼:“好高呀!”
我当时因为肿瘤压迫,右胳膊已经抬不起来,走一步都喘,却行动自若。和男生拥抱两人扭扭捏捏,旁边人都在笑。宇宇站在女生边上,我狡猾地最后向他靠近,和他近乎做做样子地拥抱完,我突然转向小辉,说:“我也搂搂你吧!”说着一把搂住,小辉在我怀里挣扎,像被捞出水的鱼儿一样扑腾。这一搂完,我就开始挨个“进攻”,顿时女生们在周围蹿上蹿下,像鸡笼里到处扑叫的小鸡。
我第二个搂的便是小云,我向她笑了笑,然后紧紧搂住她,还来回深情地晃了晃,她在我怀里好像一个轻便的玩偶,任我摇来舞去。这是当时最真实的感受。
我把能找着的人全搂了一遍,包括老师。时候不早了,该回去了,我被推着往楼里走,还在扭头想看清每个人的面孔,他们都是笑盈盈地在挥手。
后来看录像时,王钊妈妈问我是不是有生离死别的意味在里头。我笑答不是,是怕以后没理由搂了。
前些日子一个叫王正的和我同龄的少年写了一本武侠小说,名《双飞录》,破碎了我成为90后开山鼻祖的梦想。在那本书里,王正写了侠客们中伤后的疗伤,也写了少男少女们的朦胧爱情,他的体验肯定没我的刻骨铭心。
手术的时间越来越近,我的情况也越来越差。饭是一点不能吃,我享受着皇帝级别的待遇,桌子上摆满佳肴我也毫无胃口。星期四的上午,因为又出了很多节外生枝的坏事情,气氛紧张,我给小云打电话,她在家中备考,又是备考,期中考试前也是这样的情景,也是在打电话。她一接电话就说:“我本来打算下午给你打电话的。”悠哉悠哉(11) 我请她在我手术后写一些信来,能让我反复看,她肯定地答应了。
燕燕也来电话,为她星期三没能来道歉,我当时必须得吸上氧气才能舒服一些。她说老师给她们女生单独开会,指出她们心里浮躁,心里在想别的不好的事情,不安心学习了。暗示当然是明显的。我要是根据老师的标准,绝对是全世界最浮躁的人。我告诉她,让她继续浮躁下去。因为嘴上说,心里是没有改变的,连可爱的学习成绩最好的雪雪尚且会出问题,难道她不应该是全班的表率?老师不让我们对异性有感觉,大概言外之意是让我们对同性有感觉。
那天晚上,恐怕是最难熬的晚上,手上还在打着点滴,那是我最恨的东西。灯黑了,周围的病人都在睡觉,给我喝的灌肠的药水好像还没起什么作用,搞得我一会儿就得进厕所一趟,却都无功而返。我高烧不退,呼吸困难,反正所有坏情况我身上都体现着。
这时又是那个神通广大的丹云阿姨,她带来了《教父》剧本的复印件,上面还有《教父》制片人莫根写的祝福,真珍贵。
安宁也来了,就是那个上次拼命照相的女孩儿,她站在门口,还是不说话,不知道她对我的这副尊容是什么感想。妈妈事后说,这个孩子特别有爱心。当她临走的时候和我妈妈拥抱。她还是那种美国式的表达方式,是在以此来表达心情。
第二天,病房里挤满了我的亲人,我颤颤巍巍地去洗澡,结果鼻血又在狂流。我高烧不断,因为从当天0点就不能吃饭喝水,护士给我打上点滴,补充营养。爸爸拿来湿毛巾,在我脸上盘成个圈,像面包圈,又冰了头,又止了鼻血,就是形象太怪异。
马上就该“启程”了,我却关键时刻掉链子,灌肠药到这时候才起作用,爸爸只得拿着吊瓶陪我不断进厕所。我倒不怕别的,就怕在手术台上我大小便失禁就完了。
护士给我打防止唾液分泌的针,比较疼,然后就是被推着徐徐进入电梯。几天前看《半边天》讲一个女士得癌症,节目表扬了她难得的上手术台仍面带微笑的精神。我看了不以为然,我所有的照片全都是微笑的,虽然,平时人们想像着,癌症即挨整。
进了手术室,大夫们在我脚上打上点滴,我估计就是它使我睡过去的。刺眼的灯就在头顶,他们让我再说点话,我就背了When You Are Old。事后想,我要是死在手术台上,那我光辉的一生干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背诗!
当然,我到底是下了手术台的,被推出电梯时,我麻药劲没过,精神还恍惚着,但能听见妈妈在叫我。做完手术的人要先进重症监护室,有人来看我,我还是对答自如,谈笑风生,只不过现在想起来都是只记得片段,不记得全部。
夜漫漫,我迷迷糊糊地说要喝水,但还是按规定渴了30多个小时,而我渴完之后最开始喝的水你们绝想不到。那是妈妈从外面买的一瓶冰镇冰红茶,我仰脖全喝了,感觉爽极了,然后马上开始难受,要吐出来,但也没吐。
因为不是突然醒过来,而是有一个从半醒到全醒的过渡过程,我对我全身的管子不是惊奇,而是欣喜。长得像一个外星人,在口含雾化管的情况下更是如此。此时感觉是不一般的,好像身体不属于自己,尿尿没有感觉,因为有导尿管;两根引流管插在体内,也无感觉;刚做完手术的人都极其痛苦,有的人直到出院前一天还是难以入睡,让护工推着床绕着屋子转,我一点疼痛也没有(当然听相声笑除外),这福气肯定是天赐的。
在重症监护室呆到不用监护了,就进了一个两人间,很舒服。当我拔得还剩下一根引流管的时候被允许下床,在屋里稍稍走动。我坚持不让护工扶,努力站稳,享受了一会儿“腾云驾雾”的感觉,然后转头出屋子去楼道散步了,当别人还在被搀扶着一步步在楼道挪时,我就应该算是大步流星了。当时天儿正在紧张地准备高一期末考试,我就有心给她打个电话,帮她轻松一下。毕竟我已不是我。悠哉悠哉(12) 拨了号码。“喂?”正是天儿的声音。
“喂,”我故意说,“请问天儿在家吗?”
“哦!”她一惊,“稀客稀客,有失远迎。”用一个“稀客”轻松化解,生死间的这般沉重被她搞得犹如老友小别重逢。好一个天儿! 我大喊:“我的天呀!”她忙拒绝我这么喊,因为她不知道这是在叫老天爷还是在叫她。
因为经过化疗,皮肉组织与人不同,按常规该拆线了,对于我却是拆线拆早了,伤口有的地方没有长好,大夫希望我能自己愈合,就每天死命往外挤血水,再用胶布把胸部勒得紧紧的,这时我都会拿一个小镜子反照下他们的操作情况。最后实在没办法,还是重新缝过(不打麻药),期间我要求边缝能边听猫王的《温柔地爱我》。再有就是又给我做了一次胸穿,抽出了一大碗液体。
这就是术后遇到的种种麻烦,我在医院呆到最后真有些烦了。这是我在电脑上的一段随感:
“7月1日晚上,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