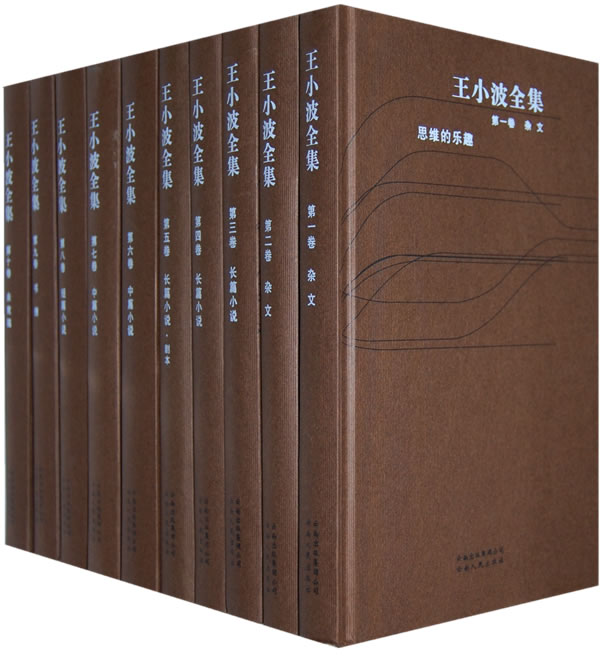**最后一张牌作者:张鼎鼎第 1 章 第一章 林跃是个二。 用菊城当地的俗语来说是二百五,用更广为人知的形容是二愣子,用现代的小资的学术用语是EQ存在明显缺陷。 这话不是谁谁往他身上泼脏水,而是经过了时间的验证的。 林跃今年二十七岁,像他这么大年龄的青年在菊城大多都成家了,就算没成家也总有个正式工作了,当然,现在经济不景气,菊城又是小城市,好工作是非常稀缺的,但是但凡有一点机会,人们都会拼命的向里钻。二十七岁的男人,没有工作,那是连老婆都娶不到的。...
有位商人,把儿子派往世界上最有智慧的人那里,去讨教幸福的秘密。这位 少年历尽艰辛。走了40天终于找到了智者那美丽的城堡。 我们的主人公走进了城堡,没有遇到一位圣人,相反,却目睹了一个热闹非 凡的场面:商人们进进出出,每个角落都有人在进行交谈,一支小乐队在演奏轻 柔的乐曲。一张桌子摆满了那个地区的美味佳肴。智者正一个个地同所有的人谈 话,所以少年必须要等上两个小时才能轮到。 智者认真地听了少年所讲的来访原因,但说此刻他没有时间向少年讲解幸福 的秘密。他建议少年在他的宫殿里转上一圈,两个小时后再来找他。...
**《沉重的翅膀》作者 张洁第一章 令人馋涎欲滴的红菜汤的香味,从厨房里飘送过来。案板上,还响着切菜刀轻快的节奏。 也许因为身体已经恢复了健康,叶知秋的心情就像窗外那片冬日少有的晴空,融着太阳的暖意。 发了几天烧,身子软软的,嘴里老有一股苦味,什么也吃不下去。 厨房里送过来的香味,诱发着叶知秋的食欲。她跟许多善良的人一样,一点儿顺心的小事,都会使她加倍地感到生活的乐趣。 比方说,一个好天气;一封盼望已久的来信;看了一部好电影;电车上有个吊儿郎当的小青年给老太太让了座现在呢,只是因为这晴朗的天;病后的好胃口...
有一天,我到某地办事,下飞机之后搭计程车。由于是初次到那个城市,就跟司机打听当地的情形。他除了为我介绍,还发表了不少对时局的看法,两人谈得很投机。 到达目的地,表上是180元。“给100元好了!”他居然手一挥,豪爽地说。“那怎么成?” 我递过去200元说:“不用找了!”就跳下车。听到他在背后连声喊着“谢谢、谢谢”,觉得好温馨。 办完事,我又叫车回机场。机场到了,计程表上的数字是120元,我真是哭笑不得,发现和前一位司机虽然谈得投机,但在谈的时候,他发现我是外来客,也就大绕远路。加上我给他的小费,足足多要了我80元。...
没有妹妹有个侄女也好。侄女弹性大:有时候我把芬芳当成我想像中的妹妹, 有时候拿她暂时充作我的独生女儿。因为我俩长得如此想像,我们的工作证和身 份证甚至可以混用。 其实她还是我的同事,却不愿意公开承认我是她的姑姑。因为这样她就矮了 一辈儿了,被迫管我们部门的人叫叔叔阿姨。最年轻的一个是刚大学毕业的实习 生,比她还要小两岁呢,却追着赶着让芬芳喊他“叔叔”。所以芬芳见了我们部 门的人总是躲着走。幸亏大楼有东西两部电梯,她做组版编辑,下午四点才上班, 那时我已经回到家中了。...
**《历史是个什么玩意儿2袁腾飞说中国史下》目录第一章落魄挨打奈何天(鸦片战争)1穷玩火富玩烟有夷称不服/弓箭对火器/女皇来贩烟/炮火中相逢/我意与君和/狮子滚绣球2大敌进逼,避暑第一找来的事端/打来的地盘/留守的亲王/劫难的中华3太平城里太平军上帝爱疯狂/兔子见到鹰/财色与天齐/天国要燃烧/蚊子衔秤砣/王多如牛毛/老虎住进城/家家都关门/自有降魔人4潮人看世界开眼第一人/花在墙外香/三郎赞西洋/学习些皮毛...
我第3次见到那小女孩时,她依然穿着那套虽然陈旧却干净的牛仔服。她弓着身子 ,拿着一块深灰色的抹布擦洗着我的车轮,蹲在地上的她显得瘦小单薄。 我拍拍她的短发,她惊恐地站起来,将双手反背在身后,红着脸说:“您好!莫伦 先生,我叫莎丽尔。”我一边打开车门,一边掏钱打算付给莎丽尔小费,但是莎丽 尔却紧张地摇头说:“对不起,莫伦先生,我并不是想要您的钱。”我将刚打开的 门重新关上,看着紧张而羞怯的莎丽尔开玩笑说:“难道你是想跟我交朋友?”她 “咯咯”地笑:“因为您跟我爸长得很像!”...
大学时代,我认识了一个年轻人。他脸上有一块巨大而丑陋的胎记。紫红的胎记从它的左侧脸角一直延伸到嘴唇,好像有人在他脸上竖着划了一刀。英俊的脸由于胎记而变得狰狞吓人。但外表的缺陷掩盖不了这个年轻人的友善,幽默,积极向上的性格,凡是和他打过交道的人,都会不由自主地喜欢上他。他还经常参加演讲。刚开始,观众的表情总是惊讶,恐惧,但等到他讲完,人人都心悦诚服,场下掌声雷动。 每到这时,我都暗暗叹服他的勇气。那块胎记一定曾带给他深深的自卑,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克服这么样中的心理障碍,在众人惊异的目光里言谈自如。...
一 汉斯?克里斯蒂安?安徒生于1805年4月2日出生在欧登赛,但谁也不知道他诞生的确切地点。 欧登赛是菲英岛上最重要的城镇,是仅次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第二大城市,200年前仅有5000位居民。这座城市贫富十分悬殊,虽然城市里住着各式各样的有钱,但半数以上的居民属于贫苦阶层,处于极端之中。在欧登塞的偏僻街道和小巷里,居住着许多贫穷的工匠、临时工、洗衣女工、乞丐和被社会遗弃的人。这就是安徒生的生活环境。 安徒生的父亲是一个鞋匠,它属于工匠的最底层。按当时的观点来看,安徒生的出身属于下层社会的最底层,这里充斥着难以忍受的贫困、贫民窟、道德败坏和淫乱。祖母是一个病态的说谎者,祖父精神失常,母亲最后成为酒鬼,姨母在哥本哈根开妓院,而他自己多年来一直知道在某处有一个同母异父的姐姐,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突然出现在眼前与他拥抱...
2003年5月1日,土耳其东南部宾格尔省迪亚巴克尔地区发生里氏6.4级地震。5月2日清晨,当救援人员将一位身受重伤的孕妇从废墟中抢救出来时,这位名叫珊德拉的女教师忍着伤痛指着废墟说,她的丈夫还埋在下面,而且仍然活着。然而,当救援人员费尽周折将她的丈夫从废墟中挖掘出来时,发现他已经死亡,他身旁放置的一部电池能量即将耗尽的录音笔却仍在转动,里面不时传来他的声音,言语中充满了对妻子的鼓励和深情厚意。虽然事情已经过去一年了,但这段绝美如诗的爱情留言故事仍在土耳其流传 陷入可怕的人间“地狱” 雷米和珊德拉结婚已经两年了,雷米是土耳其宾格尔省迪亚巴克尔地区的一家小报记者,珊德拉是一名中学教师。2003年4月30日,这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。下午,珊德拉很早就买好了晚餐需要的食物,她要为雷米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。可当珊德拉回家准备好饭菜后,却迟迟等不到雷米回家的脚步声。她从7点一直等到11点,...
一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,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,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。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,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,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,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。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,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。 从窗框伸出的铁皮烟筒悠悠地冒出一缕缕淡灰的煤烟,火炉正在烘除屋子里整个一个冬天积攒的寒气。我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到小院,南窗前的丁香和东西围墙根下的三株枣树苗子,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,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,显然是春天的讯息。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,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。...
1 再过一百年,人们会这样描述现在的北京城:那是一大片灰雾笼罩下的楼房,冬天里,灰雾好象冻结在天上。每天早上,人们骑着铁条轮子的自行车去上班。将来的北京人,也许对这样的车子嗤之以鼻,也可能对此不胜仰慕,具体怎样谁也说不准。将来这样的车子可能都进了博物馆,但也可能还在使用,具体会怎样谁也说不准。将来的人也许会这样看我们:他们每天早上在车座上磨屁股,穿过漫天的尘雾,到了一座楼房面前,把那个洋铁皮做的破烂玩艺锁起来,然后跑上楼去,扫扫地,打一壶开水,泡一壶茶,然后就坐下来看小报,打呵欠,聊大天,打瞌睡,直到天黑。但是我不包括在这些人之内。每天早上我不用骑车上班,因为我住在班上。我也不用往楼上跑,因为我住在地下室,上班也在地下室,而且我从来不扫地。我也不打开水,从来是喝凉水。每天早上我从床上起来,坐到工作台前,就算上了班。这时候我往往放两个响屁,标志着我也开始工作了...
第一回 你好,雪碧手机响起来的时候,我正好督见了公路边那个沉默的“70”,于是我发现,我开到了100.跟着我就知道,一定是西决打来的。很奇怪,每到我犯诸如此类的小错时,比如超速,比如随地丢烟头,比如看着我儿子干净的眼睛诅咒他爸爸出车祸终身残疾,——在这样的瞬间,如果电话响了,十有八九是西决。我真不明白这种事情是怎么发生的,他又不是老天爷,为什么他的声音总能如此准时地驾到,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中,我就像是个根本没来得及偷看什么却逃不脱“作弊”罪名的倒霉孩子。“快到了么?”他语气里总是有种叫人妒忌的闲散。...
美国马里大学神经生物学和心理学教授罗伯特·普洛文却发现事实并非如此。他把近10年来的精力倾注于对笑的研究中,并将其结果 —— 什么是笑,为什么人们会笑得这么厉害和频繁等发表于《笑的科学》一书中。普洛文开始观察那些偶然的谈话,并同时计算当一个人谈话时笑的次数。观察结果使他发现了一些新问题。普洛文说道:“我开始记录下所有这些谈话,我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:说者要比听者笑得频繁得多。” 记录结果显示:讲话的人发笑的可能性要比听众高出约46%。不仅如此,能够引人发笑的句子中只有15%在传统意义上是幽默的。除此之外的大笑与幽默毫无关系,而是一种辅助强调社会关系的工具。...
近来涉猎了不少名人传记,其中戏剧家曹禺的一则逸闻引发了我的好奇心。 上世纪80年代,年逾古稀的曹禺已是海内外声名鼎盛的戏剧作家。有一次美国同行阿瑟·米勒应约来京执导新剧本,作为老朋友的曹禺特地邀请他到家做客。吃午饭时,曹禺突然从书架上拿来一本装帧讲究的册子,上面裱着画家黄永玉写给他的一封信,曹禺逐字逐句地把它念给阿瑟·米勒和在场的朋友们听。这是一封措辞严厉且不讲情面的信,信中这样写到:“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,一个也不喜欢。你的心不在戏剧里,你失去伟大的灵通宝玉,你为势位所误!命题不巩固、不缜密、演绎分析也不够透彻,过去数不尽的精妙休止符、节拍、冷热快慢的安排,那一箩一筐的隽语都消失了”...
索菲·蒙特娜是音乐天才。3岁时在微型木琴上模仿弹奏电视广告曲,父母连劝带哄才能把她从高高的琴凳上抱到饭桌前。她的父母在中国工作过,经常给她讲“狼来了”的故事。教她要诚实,不说谎话。蒙特娜聪明而刻苦,14岁练习贝多芬“命运交响曲”,竟把手指磨出老茧。 15岁那年冬天,天气特别冷,因晚上坚持迎着暴风雪去上钢琴课而患了肺炎。 她住进了汉诺威医院。病床左面是位女教师,右面是位文化不高的老太太。女教师的女儿是医生。对母亲的病历总是严密收藏。 有一天,女儿不在,小护士竟把ECT(加强CT)诊断报告稀里糊涂地送到女教师手中。她见报告上写着:肝Ca(癌症的缩写)晚期。这无疑是一纸死亡宣判书。她掩面而泣,一头倒在床上再也没起来。由于精神崩溃,半月后便离开了人间。...
她刚从国外回来,与丈夫一块儿回来度假。回家的感觉真的很好,可惜心中 总有那么一丝疼痛。事情虽然过去两年了,虽然是一千一万个不愿意,她还是去 找了负心的他。 “在国外习惯吗?”“还好。你呢?”“哦——也还好。”淡淡的两个人都 不知道怎么开口了。 他是她的前夫,相爱的日子,波澜不惊,却十分温馨。两人是大学的同学, 毕业就结婚了,没有特别的成就,无忧无虑。日子一天天的过去,当两个人都以 为生活就这样不会有什么改变的时候,一件事情发生了。 他被查出患有绝症,一下子好象什么都改变了。他停止了工作,住院治疗。...
:** 我的搭档,宛如我情人一般的责编——哲夫②,也成了不管到哪儿都受欢迎的明星。斗转星移,曾经多情(?)的我也终于嫁作人妻。然而追逐流行的喜好、冲动的购买欲还是一如往昔。哲夫依然独身,一直翘首期盼着我的离婚(开开玩笑)。他英俊又有名气,年龄虽在增长,人却越来越帅气,知识分子的酸劲儿已经消退净尽,开始具备成熟深沉的男人气质。不过,年轻人中知道哲夫这个名字的毕竟还是少数。 我想起另一件事,就在不久前还为《安安》杂志这个栏目执笔的柴门文③女士最近明显地靓丽起来。她本来就五官端正,最近穿戴和打扮又越来越文雅,还加上了许多流行的装束。...
小学,我学了加减乘除和几百个汉字。中学,我学了一元二次方程和牛顿第二定律。大学,我学了普通物理和理论物理。硕士,我学了酶和DNA复制。博士,我学了微观经济、宏观经济和企业管理。历时二十多年,人生的1/4或许还多,我都投资在了学习上。教我的老师中有男老师、女老师;有历经沧桑的老老师,有刚刚步入人生的年轻老师;有中国老师、美国老师、加拿大老师、德国老师、印度老师和墨西哥老师。可是,如此漫长的时间和如此众多的老师,却没人教我什么是生活,没人教我懂得自己,也没人教我该从生活中获得什么。 不懂生活的我走出了校门,心中装满了许多的迷惑。迷惑中,我又开始了探索,探索的目的只有一个,我要找到一个好老师,让他或她教我懂得生活,使我从此不再迷惑。...
小时候上幼儿园,老师必须把我的坐位单独排在窗口。因为如果不能一直凝视着窗外,我就会哭闹不休,搞得别的小孩无法上课。于是从四岁到六岁,我是对着窗外度过我人生最早的学校生涯的。 世界,就在窗户的外面。 幼小的我不会这么想,却执拗地只愿意面对窗外那个有人走过,有云和树叶飘过的光影变幻的世界,而不愿意回头接受窗子里这种被规定,被限制的小小人生。令人头痛的是,长大之后的我竟然也是这样。 我没办法接受人生里许多小小的规矩。进小学,我读不会课本,做不了功课,念中学,我被好几所学校踢来踢去,上大学,我是自己关着门读了几个月书奇迹般考上的,等退伍有一份好工作后,我却跑去做当时还没有人认同的专职漫画家。就像小时候一样,别人上班,上课,我却只想一直看着,或接触窗户外面那个流动的世界。...